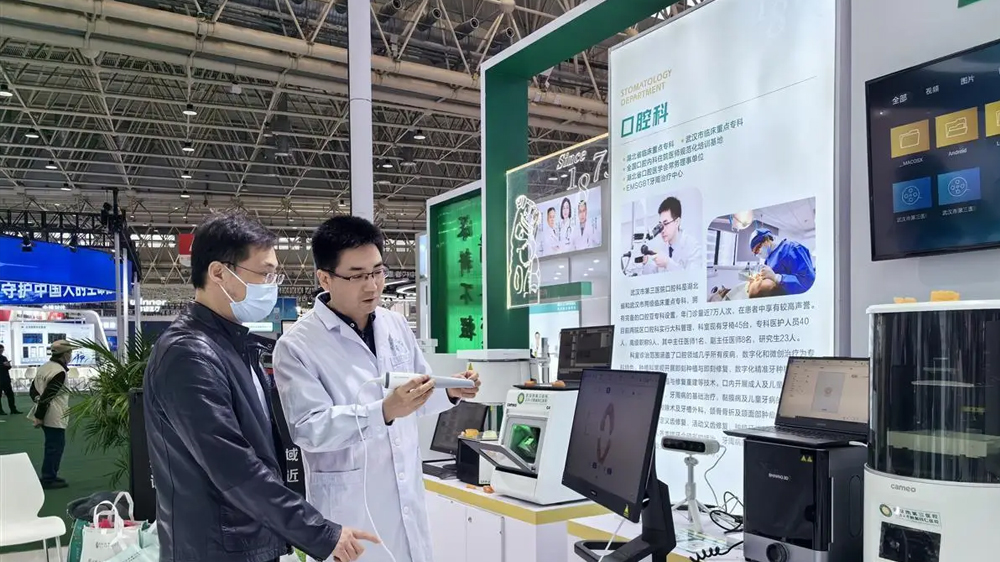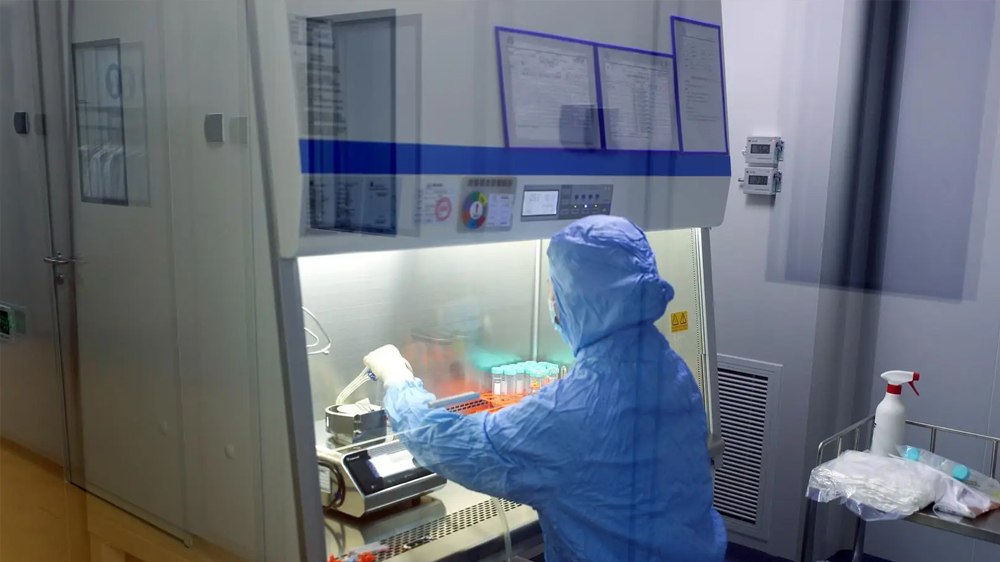йҘҘйҘҝзҡ„иҖіжңө
жӣ№жҳҘйӣ·
иҖіжңөд№ҹжҳҜдјҡйҘҘйҘҝзҡ„пјҢдёҚиҝҮиҖіжңөзҡ„йҘҘйҘҝдёҚжҳҜеӣ дёәеҗ¬еҫ—еӨӘе°‘пјҢиҖҢжҳҜеҗ¬еҫ—еӨӘеӨҡпјҢдё”еҗ¬еҲ°зҡ„еӨҡжҳҜдёҚжғіеҗ¬зҡ„еЈ°йҹігҖӮиӯ¬еҰӮдёҖдёӘдәәйқўеҜ№зқҖдёҖжЎҢиҮӘе·ұеҫҲдёҚе–ңж¬ўпјҢз”ҡиҮіиҰҒеҸҚиғғзҡ„иҸңпјҢеҚҙдёҚеҫ—дёҚеҗғдёӢеҺ»пјҢжңҖеҗҺиғғжҳҜйҘұдәҶпјҢдҪҶеҝғеҚҙдёҖзӣҙжҳҜйҘҘйҘҝзҡ„гҖӮ
дёҖеҸҢеҹҺеёӮзҡ„иҖіжңөпјҢжіЁе®ҡжҳҜиҝҷж ·йҘұзқҖдё”йҘҘйҘҝзқҖзҡ„гҖӮжұҪиҪҰйёЈз¬ӣеЈ°гҖҒе•Ҷй“әе–ҮеҸӯеҸ«еҚ–еЈ°гҖҒе·Ҙең°ж–Ҫе·ҘеЈ°гҖҒйӮ»еұ…иЈ…дҝ®еЈ°гҖҒе№ҝеңәиҲһжӣІеЈ°вҖҰвҖҰе®ғ们зҺҜз»•еңЁж—ҒпјҢеҰӮдёҖж”Ҝж”Ҝй”җеҲ©зҡ„зҹӣпјҢдёҖжіўдёҖжіўеҗ‘иҖіжңөеҸ‘еҠЁиҝӣж”»пјҢиҖҢеҸҜжҖңзҡ„иҖіжңөпјҢжҜ«ж— жӢӣжһ¶д№ӢеҠӣгҖӮ
жҹҗеӨ©жҷҡдёҠпјҢжҲ‘еқҗеңЁд№ҰжЎҢеүҚеҶҷзЁҝпјҢе…ізҙ§дәҶй—ЁзӘ—пјҢдҪҶйҷ„иҝ‘е№ҝеңәиҲһжӣІеЈ°дҫқ然еӣәжү§ең°д»Һй—ЁзјқгҖҒзӘ—зјқйҮҢй’»иҝӣжқҘпјҢи®©жҲ‘зҡ„иҖіжңөдёҚеҫ—е®үе®ҒгҖӮжҲ‘з”ҡиҮід№°дәҶиҖізҪ©жҲҙпјҢдҪҶеҝғйҮҢеҚҙж„ҹи§үе№ҝеңәиҲһжӣІеЈ°дҫқ然иҗҰз»•еңЁиҖіж—Ғ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жҲ‘еҪ»еә•еҗ‘иҝҷеЈ°йҹіжҠ•йҷҚвҖ”вҖ”жҳҜзҡ„пјҢдҪ иөўдәҶгҖӮ
иҝҷж—¶еҖҷпјҢжҲ‘ж— жҜ”жҖҖеҝөд»ҘеүҚеңЁд№Ўжқ‘зҡ„йӮЈдәӣеӨңжҷҡгҖӮйӮЈж—¶зҡ„еӨңжҷҡпјҢеӨҡйқҷе•ҠпјҢж•ҙдёӘжқ‘еә„йқҷеҫ—е°ұеғҸдёҖйқўж·ұйӮғзҡ„ж№–пјҢдёҖдёӨеЈ°зӢ—еҗ е“Қиө·пјҢе°ұеғҸдёҖзІ’зҹіеӯҗжҠ•еңЁж№–дёҠпјҢж№–ж°ҙжіӣиө·еҮ еңҲж¶ҹжјӘеҗҺпјҢжқ‘еә„жӣҙеҠ е®ҒйқҷгҖӮ并дёҚжҳҜдёҮзұҒдҝұеҜӮпјҢзҒҜдёӢпјҢжҳҜжңүиҚүиҷ«йёЈзҡ„пјҢиҚүиҷ«д»¬еңЁжј”еҘҸдәӨе“Қд№җпјҢиҷҪдҪҺжІүеҚҙзӣӣеӨ§зҡ„дәӨе“Қд№җгҖӮ
иӢҘеңЁеұұй—ҙпјҢвҖңдәәй—ІжЎӮиҠұиҗҪпјҢеӨңйқҷжҳҘеұұз©әвҖқпјҢеҜӮйқҷеҫ—иғҪеҗ¬и§ҒжЎӮиҠұиҗҪең°зҡ„еЈ°йҹігҖӮвҖңз©әеұұжқҫеӯҗиҗҪпјҢе№Ҫдәәеә”жңӘзң вҖқпјҢдёҖзІ’жқҫеӯҗз ёеңЁең°дёҠзҡ„еЈ°йҹіпјҢд№ҹиғҪиў«дёҖеҸҢе®Ғйқҷзҡ„иҖіжңөжҚ•жҚүеҲ°гҖӮ
йҖҷжҳҜеӨңй—ҙзҡ„еӨ©зұҒгҖӮ
еҚідҪҝеңЁзҷҪеӨ©пјҢжқ‘еә„д№ҹжҳҜйқҷзҡ„гҖӮиҷҪ然вҖңзӢ—еҗ ж·ұе··дёӯпјҢйёЎйёЈжЎ‘ж ‘йў вҖқпјҢиҷҪ然зүӣеЈ°е“һе“һпјҢзҫҠзҫӨе’©е’©пјҢдҪҶиҝҷдёҖзӮ№е„ҝд№ҹдёҚи®©дәәз”ҹеҺҢпјҢеҸӘдјҡи®©дәәж„ҹеҸ—еҲ°з”°еӣӯж°”жҒҜзҡ„жө“йғҒгҖӮеҰӮжһңиҜҙиҖіжңөжңүиЎЁжғ…зҡ„иҜқпјҢйӮЈд№ҲжӯӨж—¶е®үдәҺжқ‘еә„зҡ„иҖіжңөдёҖе®ҡжҳҜеҫ®з¬‘зқҖзҡ„пјҢеҫ®з¬‘зҡ„иҖіжңөдёҖе®ҡжҳҜе®үйҖёзҡ„пјҢе®үйҖёеҰӮеўҷеӨҙдёҠдёҖеҸӘеҚ§зқҖеҒҮеҜҗзҡ„зҢ«гҖӮ
иӢҘжҳҜйӣЁеӨ©пјҢеқҗеңЁеұӢжӘҗдёӢпјҢзңӢйӣЁжү“зҹійҳ¶пјҢеҗ¬йӣЁжү“йқ’з“ҰпјҢиҖіжңөжҳҜжё…зҲҪзҡ„пјҢеҝғд№ҹжҳҜжё…зҲҪзҡ„гҖӮжӯӨж—¶пјҢз“ҰжҳҜзҗҙй”®пјҢйӣЁжқҘеј№еҘҸгҖӮйҡҸзқҖйӣЁеҠҝзҡ„еӨ§е°ҸпјҢиҝҷзҗҙеЈ°ж—¶иҖҢдҪҺеӣһпјҢж—¶иҖҢй«ҳдәўпјҢжңүж—¶еҰӮе°ҸжЎҘжөҒж°ҙпјҢжңүж—¶еҸҲеҰӮжҲҳйј“иҪ°йёЈгҖӮзӘ—еӨ–иӢҘжҳҜз«№жһ—пјҢжӣҙзҫҺгҖӮйӣЁжү“з«№еҸ¶пјҢйЈҺиҝҮз«№жһ—пјҢжІҷжІҷжІҷпјҢеҰӮиҡ•еҗғжЎ‘еҸ¶пјҢеҰӮж·ҷж·ҷжөҒж°ҙгҖӮ
жүҖд»ҘиҜҙпјҢд№Ўжқ‘зҡ„иҖіжңөпјҢжҳҜжңүзҰҸзҡ„гҖӮ
д№Ўжқ‘зҡ„иҖіжңөд№ҹжёҙжңӣиҝӣеҹҺпјҢдҪҶеҪ“е®ғиҝӣеҹҺеҗҺпјҢжүҚз»ҲдәҺеҸ‘зҺ°еҹҺеёӮеҜ№иҮӘе·ұжқҘиҜҙж„Ҹе‘ізқҖд»Җд№ҲгҖӮеҪ“е№ҙпјҢжҲ‘жІЎи§ҒиҝҮзҒ«иҪҰпјҢи·‘иҖҒиҝңеҺ»зңӢзҒ«иҪҰпјҢеҗ¬зҒ«иҪҰе’ЈеҪ“е’ЈеҪ“驶иҝҮпјҢдёәиҝҷе®ҸеӨ§зҡ„ж°”еҠҝжүҖйңҮж’јгҖӮзҹҘйҒ“зҒ«иҪҰзҡ„з»ҲзӮ№жҳҜеҹҺеёӮпјҢдәҺжҳҜеҜ№еҹҺеёӮе……ж»ЎдәҶеҗ‘еҫҖ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й•ҝеӨ§еҗҺиҝӣе…ҘеҹҺеёӮжү“жӢјпјҢз§ҹжҲҝпјҢдҪҸеӨ„зҰ»зҒ«иҪҰйҒ“дёҚиҝңпјҢеӨңеҚҠж—¶зҒ«иҪҰйҡҶйҡҶ驶иҝҮпјҢеӨ§ең°йңҮйўӨпјҢжҲ‘д»ҺзқЎжўҰдёӯйҶ’жқҘпјҢеҶҚж— зқЎж„ҸгҖӮжӣҫеҜ№зҒ«иҪҰжңүиҝҮзҡ„зҫҺж„ҹпјҢжӯӨж—¶ж¶ҲеӨұеҫ—ж— еҪұж— иёӘгҖӮ
дҪң家зҺӢејҖеІӯиҜҙпјҢзҺ°д»Јдәәзҡ„зү№еҫҒжҳҜпјҡжәәзҲұеҳҙе·ҙпјҢе® е№ёзңјзқӣпјҢиҷҗеҫ…иҖіжңөгҖӮвҖңи®әеҗғе–қпјҢжҲ‘们йЈҹдёҚеҺҢзІҫгҖҒи„ҚдёҚеҺҢз»ҶпјҢеҚҺеӨҸд№ӢйӨ®пјҢдёҫдё–ж— еҸҢгҖӮи§Ҷи§үдёҠпјҢзҫҺиүІгҖҒжңҚйҘ°гҖҒиҠұиҚүгҖҒж©ұзӘ—гҖҒе№ҝеңәгҖҒйң“иҷ№пјҢжүҖжңүзҡ„ж—¶е°ҡе®ЈиЁҖе’ҢзҺҜеўғдё»еј ж— дёҚеңЁвҖҳиүІзӣёдёҠдёӢеҠҹеӨ«гҖӮвҖқ
з»ҲдәҺжңүдёҖеӨ©пјҢжҲ‘зҡ„иҖіжңөдёҚе Әиҝҷиҷҗеҫ…пјҢиҜ·жұӮжҲ‘иғҪдёҚиғҪеӨҡеёҰе®ғеҲ°е®үйқҷзҡ„ең°ж–№еҺ»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жҲ‘еёёй©ұиҪҰеҮәеҹҺпјҢеҲ°йғҠеӨ–дёҖеә§еұұдёҠеҺ»пјҢйӮЈйҮҢпјҢжһ—ж·ұпјҢж ‘еҜҶпјҢйёҹеӨҡпјҢдәәе°‘гҖӮжҲ‘еқҗеңЁйқ’зҹідёҠпјҢзңӢжәӘжөҒпјҢеҗ¬жқҫж¶ӣпјҢеҗ¬йёҹйёЈгҖӮ
жҜҸж¬ЎеҺ»пјҢйғҪжҳҜиҖіжңөзҡ„дёҖеңәзӣӣе®ҙгҖӮ
пјҲзј–иҫ‘ 欣然пј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