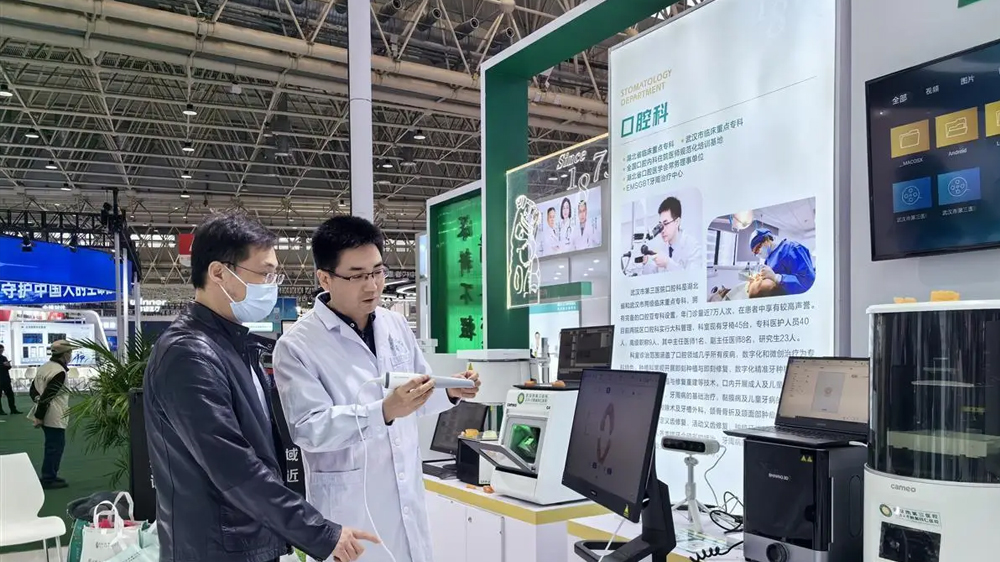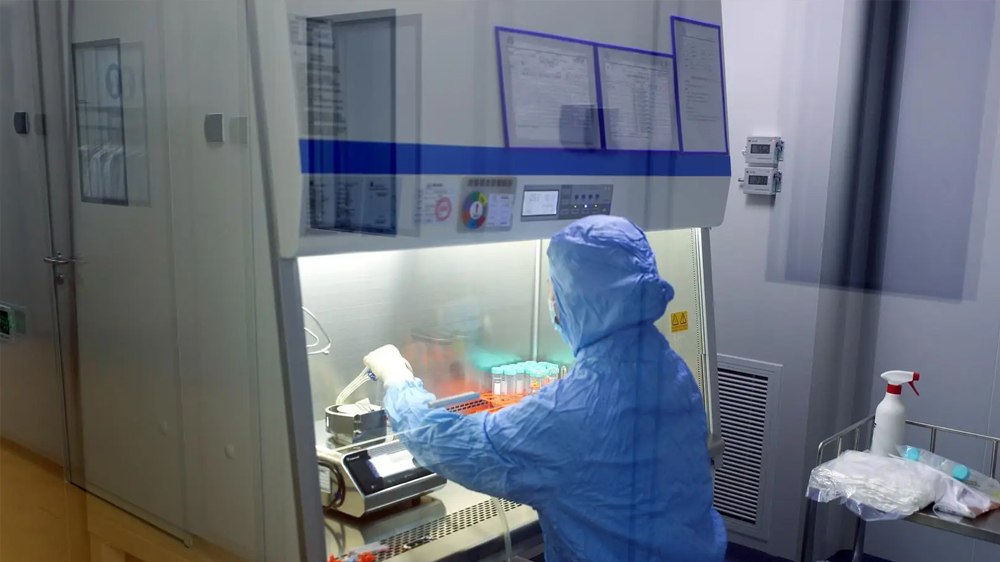иҫ№и§’ж–ҷзҡ„жё©еәҰ
еј жҷҙйӣҜ
еӣ дёәе·ҘдҪңзҡ„зјҳж•…пјҢжҗңйӣҶж•ҙзҗҶеҲ°дәҶдёҖдәӣж°‘еӣҪж—¶жңҹзҡ„ж–ҮеҸІиө„ж–ҷгҖӮе®ғ们дёҚеңЁеҸІд№ҰдёҠпјҢдёҚеңЁж–№еҝ—йҮҢпјҢжӣҙдёҚжҳҜжү“ејҖжүӢжңәжҲ–иҪ»зӮ№йј ж Үе°ұеҸҜд»ҘвҖңзҷҫеәҰвҖқеҲ°зҡ„дёңиҘҝгҖӮйӮЈжҳҜдәӣеҺҶеҸІзҡ„иҫ№и§’ж–ҷпјҢйӣ¶йӣ¶ж•Јж•ЈпјҢзҗҗзҗҗзўҺзўҺпјҢеңЁж— иҫ№еІҒжңҲзҡ„и§’иҗҪйҮҢжІүй»ҳдёҚиҜӯгҖӮ
жІЎжғіеҲ°е°ұжҳҜиҝҷж ·дёҖдәӣй»ҳй»ҳж— й—»зҡ„иҫ№и§’ж–ҷпјҢеҚҙи®©жҲ‘з©ҝи¶Ҡж—¶з©әпјҢи§Ұж‘ёеҲ°дёҚе°‘з”ҹе‘Ҫзҡ„жё©еәҰгҖӮ
и”Ўе°ҡжҖқжҳҜи‘—еҗҚзҡ„еҺҶеҸІгҖҒж–ҮеҢ–гҖҒжҖқжғіеҸІеӯҰ家пјҢжӣҫд»»еӨҚж—ҰеӨ§еӯҰеүҜж Ўй•ҝгҖӮд»–еӯҰжңҜи‘—дҪңзӯүиә«пјҢдёҖеәҰдёҺй’ұй’ҹд№ҰйҪҗеҗҚпјҢзҙ жңүвҖңеҢ—й’ұеҚ—и”ЎвҖқд№Ӣз§°гҖӮиҝҷж ·дёҖдёӘд»ҘеӯҰжңҜи‘—з§°зҡ„дәәпјҢеә”иҜҘжҳҜдёӘи°Ұи°ҰеӯҰиҖ…еҗ§пјҹдёҚжғіеҚҙжңүзқҖй“®й“®й“ҒйӘЁгҖӮд»–д»Һе°Ҹе°ұдёҚе№ідәҺз”·е°ҠеҘіеҚ‘пјҢдёәдәҶгҖҠи®әиҜӯгҖӢдёӯзҡ„вҖңе”ҜеҘіеӯҗдёҺе°Ҹдәәйҡҫе…»д№ҹвҖқдёҺз§ҒеЎҫиҖҒеёҲеҗөжһ¶пјҢиҝҳеӣ дёәжҜҚдәІе§“йғӯиҖҢ改用笔еҗҚвҖңйғӯз”ҹвҖқпјӣе°‘е№ҙ时家乡зҲ¶иҖҒд»ҘвҖңе°Ҹең°ж–№зҡ„дәәпјҢдёҚеҸҜиғҪеҒҡеҮәеӨ§дәӢдёҡвҖқгҖҒвҖңзҲ¶жҜҚеңЁпјҢдёҚиҝңжёёвҖқзӯүзӯүдёәз”ұеҠӣйҳ»д»–еҢ—дёҠжұӮеӯҰпјҢд»–еҲҷеә”д»ҘвҖңйӮЈжҳҜең°зҗҶе‘Ҫе®ҡи«–пјҢжҲ‘дёҚдҝЎвҖқвҖңжҲ‘еҶідёҚеҪ“еӯ”еӯҗе’ҢзҲ¶дәІзҡ„еҘҙжүҚвҖқпјҢз”ҡиҮід»ҘиҮӘжқҖжҠ—дәүгҖӮ
дёҖдёӘдәәеңЁиҗҪйӯ„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жңҖиғҪзңӢеҮәжң¬иҙЁеҗ§пјҹеҚідҫҝжҳҜеңЁеӨұдёҡ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и”Ўе°ҡжҖқдёҖж ·дёҚеҝҳеҲқеҝғгҖӮд»–е№Іи„ҶжӢҺдәҶеҢ…иўұпјҢдёҖж•ҙе№ҙе…ҘдҪҸеҚ—дә¬еӣҪеӯҰеӣҫд№ҰйҰҶпјҢеңЁжӮЈжңүзңјз–ҫ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вҖңжҜҸеӨ©иҮіе°‘з”ЁеҚҒе…ӯдёӘе°Ҹж—¶вҖқпјҢиҮӘиӘ“вҖңжҠҠйҰҶи—ҸжүҖжңүж–ҮйӣҶиҜ»е®ҢвҖқгҖӮеӣ дёәж”ҝи§ҒдёҚеҗҢпјҢеӣҪж°‘ж”ҝеәңж•°ж¬Ўд»Ҙе·ҘдҪңиҒҢдҪҚеҗ‘д»–дјёжқҘж©„жҰ„жһқпјҢд»–еқҮдёҚж„ҝеә”иҒҳпјӣе№ҝе·һдёҖдёӘеӯҰжө·д№ҰйҷўпјҢж¬Ід»ҘйҮҚйҮ‘йӮҖд»–жҢҮеҜјз ”究з”ҹпјҢд»–еҚҙеӣ еӯҰйҷўвҖңжҸҗеҖЎе°Ҡеӯ”иҜ»з»ҸпјҢдёҺжҲ‘жҖқжғіеҜ№з«ӢвҖқиҖҢж–ӯ然дәҲд»ҘжӢ’з»қгҖӮ
вҖ”вҖ”иҝҷе°ұжҳҜвҖңдёҚдёәдә”ж–—зұіжҠҳи…°вҖқпјҒеңЁи”Ўе°ҡжҖқз®ҖжҙҒжңҙзҙ зҡ„иҮӘдј жҖ§ж–Үеӯ—дёӯпјҢдёҖдёӘдј з»ҹ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зҡ„жҠұиҙҹдёҺиЎҖжҖ§пјҢе°ұиҝҷж ·еңЁжІЎжңүдёқжҜ«еҚҺдёҪиҫһи—»зҡ„еӯ—йҮҢиЎҢй—ҙз«ҷдәҶиө·жқҘгҖӮ
еӣҪж°‘е…ҡйҷҶеҶӣе°‘е°ҶеҫҗдјҡжҳҘжҳҜзӣ–еҫ·дёүзҰҸжқ‘дәәпјҢжӣҫеҸӮеҠ ж·һжІӘдјҡжҲҳзӯүеӨҡеңәйҮҚеӨ§жҲҳеҪ№гҖӮд№ҹи®ёеӣ дёәж”ҝжІ»иә«д»Ҫзҡ„зјҳж•…пјҢд»–зҡ„еӣһеҝҶеҪ•зӣёеҪ“дҪҺи°ғпјҢеҸӘжҳҜжҲҳдәӢиҝҮзЁӢзҡ„з®ҖеҚ•еҸҷиҝ°е’Ңеҝ…иҰҒзҡ„ж•°еӯ—и®°еҪ•пјҢжІЎжңүдёҖзӮ№дёҖж»ҙвҖңеҸұе’ӨйЈҺдә‘вҖқвҖңжІҷеңәзӮ№е…өвҖқзҡ„еЈ®еҝ—дёҺиұӘжғ…гҖӮз”ұдәҺвҖңи§Јж”ҫеҚ—дә¬вҖқдёҖжҲҳдёӯиў«еӣҪж°‘е…ҡж”ҝеәңе®ҡзҪӘвҖңејҖж”ҫй•ҝжұҹж’ӨиҒҢжҹҘеҠһвҖқпјҢд»–еңЁжҲҳеҗҺжҪңйҖғеӣӣе·қйҮҚеәҶгҖӮи§Јж”ҫеҗҺд»–жөҒиҗҪжӯҰжұүпјҢж‘ҶиҝҮең°ж‘ҠпјҢеҚ–иҝҮиҢ¶еҸ¶пјҢеҪ“иҝҮе·ҘеҺӮзҡ„дјҡи®ЎдёҺеҮәзәіпјҢй—ІжҡҮд№ӢдҪҷеҶҷдәӣеӣһеҝҶеҪ•пјҢ
иөҡеҸ–зЁҝиҙ№д»ҘиҙҙиЎҘ家用гҖӮжғіжқҘз”ҹжҙ»зӣёеҪ“жӢ®жҚ®еҗ§пјҹдёәдәҶиҠӮзңҒзЁҝзәёпјҢд»–жҠҠеҲқзЁҝеҶҷеңЁи®°иҙҰжң¬дёҠпјҢж–Үеӯ—з»ҶеҜҶиҖҢеҸҲжӢҘжҢӨгҖӮеңЁд»…жңүзҡ„з©әзҷҪеӨ„пјҢиҝҳеҸҜд»ҘзңӢеҲ°д»–ж‘Ҷз«–ејҸи®Ўз®—ж–Үз« зҡ„еӯ—ж•°дёҺзЁҝиҙ№гҖӮ
еҫҗдјҡжҳҘжҠҠзЁҝ件еҜ„еҫҖе“ӘйҮҢпјҹж–Үз« йҮҮз”ЁдәҶеҗ—пјҹжңүжІЎжңү收еҲ°д»–ж—ҘеӨңзӣјжңӣзҡ„зЁҝиҙ№пјҹиҝҷдәӣйғҪдёҚеҫ—иҖҢзҹҘгҖӮжҲ‘зңӢеҲ°зҡ„еҸӘжҳҜд»–зҡ„иҚүзЁҝпјҢи®ёеӨҡең°ж–№еӣ дёәеӨҡйҮҚдҝ®ж”№иҖҢеӯ—иҝ№жЁЎзіҠпјҢж №жң¬ж— жі•иҫЁи®ӨгҖӮ然иҖҢйӮЈеҜҶеҜҶйә»йә»зҡ„еӯ—иҝ№е’Ңи®Өи®Өзңҹзңҹзҡ„з®—жңҜејҸпјҢеҚҙи®©жҲ‘еңЁдёҚиғңе”Ҹеҳҳд№Ӣйҷ…пјҢи§Ұж‘ёеҲ°дәҶиҖҒе°ҶеҶӣеҶ…еҝғе№Ҫеҫ®иҖҢжӣІжҠҳзҡ„еҸҰдёҖз§Қжё©еәҰгҖӮжҲ‘дјјд№ҺзңӢеҲ°дёҖдҪҚз”ҹжҙ»зӘҳеӣ°зҡ„иҖҒдәәпјҢеңЁжҳҸй»„зҡ„зҒҜе…үдёӢдёҖдёӘеӯ—дёҖдёӘеӯ—ең°ж”ҖзјҳеёҢжңӣпјҢеҚ‘еҫ®иҖҢеҸҲеқҡйҹ§еҖ”ејәең°пјҢдёәй»Ҝж·Ўзҡ„з”ҹи®ЎзӮ№зҮғеҫ®е…үгҖӮ
зҺӢе…үеј жҳҜеүҚжё…жң«з§‘д№ЎиҜ•дёҫдәәпјҢеҫ·еҢ–еҸІдёҠе”ҜдёҖдёҖдёӘж°‘йҖүеҺҝй•ҝгҖӮеҒҸеҒҸз”ҹдёҚйҖўж—¶гҖӮеҸ—е°ҒжұҹиҘҝеёғеә“еӨ§дҪҝпјҢиҝҳжІЎдёҠд»»е°ұж”№жңқжҚўд»ЈпјҢеҸҳдәҶеӨ©ең°гҖӮиҝ”еҪ’жЎ‘жў“пјҢеҚҙеҢӘд№ұзә·дәүпјҢйҡҫжұӮдёҖж—Ҙе®үе®ҒгҖӮиҷҪ然еңЁд№ұдё–дёӯиҫ—иҪ¬пјҢд»–е§Ӣз»Ҳжғ…жҖҖдёҚж”№гҖӮеңЁдёҖдәӣи®Је‘ҠгҖҒеҜҝеәҸдёҺеў“еҝ—й“ӯдёӯпјҢжҲ‘зңӢеҲ°д»–вҖңеҪ’йҡҗжһ—жіүдёүеҚҒиҪҪпјҢжҠ„д№Ұйҳ…з»Ҹж•°зҷҫеҚ·вҖқпјҢеңЁжҲҝеӯҗж—Ғиҫ№е»әйҖ вҖңйҖёеӣӯвҖқпјҢе®…еүҚз§ҚиҠұгҖҒеұӢеҗҺз§Қз«№пјҢвҖңж—Ҙж¶үжҲҗи¶ЈпјҢиҖҒиҮідёҚзҹҘвҖқпјҢвҖңйҖ еәҗиҖҢиҜ·иҖ…иҮіеҶҚиҮідёүвҖқд№ӢеҗҺпјҢд»–еҸ—йӮҖеҮәд»»еҺҝдҝқеҚ«еӣўжҖ»пјҢз«ӯеҠӣдё»еј е®үе®ҡең°ж–№гҖҒеҸ‘еұ•з”ҹдә§пјҢиҝҳи‘—ж–ҮеҶҷиҜ—е‘ҠиҜ«еҗ„ең°ж°‘еҶӣйҰ–йўҶиҰҒвҖңеҝғз”°з§Қеҫ·пјҢеӢҝж®Ӣз”ҹзҒөвҖқпјӣд»–дё»еҠһе…»жөҺйҷўжҺЁиЎҢе–„дәӢпјҢеҮЎжҳҜж— дё»е°ёдҪ“пјҢжҲ–еӣ 家еўғиҙ«еҜ’дәІдәәж— еҠӣ收еҹӢиҖ…пјҢд»–еқҮж–ҪжЈәиө„еҠ©ж”¶еҹӢпјҢвҖң5е№ҙж–ҪжЈәзҷҫйғЁвҖқгҖӮ
йҡҫжҖӘеҗҢдёәдёҫдәәзҡ„иҜ—дәәйғ‘зҝҳжқҫиөһеҸ№е…¶вҖңжҠұдёҖиҜҡгҖҒе®ҲдёҖеҫ·гҖҒдё“дёҖз»ҸгҖҒжү§дёҖиүәпјҢдҝ®д№ӢдәҺиә«пјҢеҢ–д№ӢдәҺд№ЎпјҢиҮӘеЈ®иҮіиҖҒпјҢдёҚж”№е…¶ж“ҚвҖқпјҢеғҸиҝҷж ·зҡ„жғ…жҖҖдёҺжӢ…еҪ“пјҢе…¶иғҢеҗҺж•ЈеҸ‘еҮәжқҘзҡ„е…үе’ҢзғӯпјҢеҚідҫҝеңЁеҪ“д»Ҡзӣӣдё–еҗ§пјҢеҸҲжңүеҮ дәәиғҪеҸҠпјҹ
пјҲеёёжң”ж‘ҳиҮӘгҖҠзҰҸе»әж—ҘжҠҘгҖӢ2016е№ҙ1жңҲ13ж—Ҙпј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