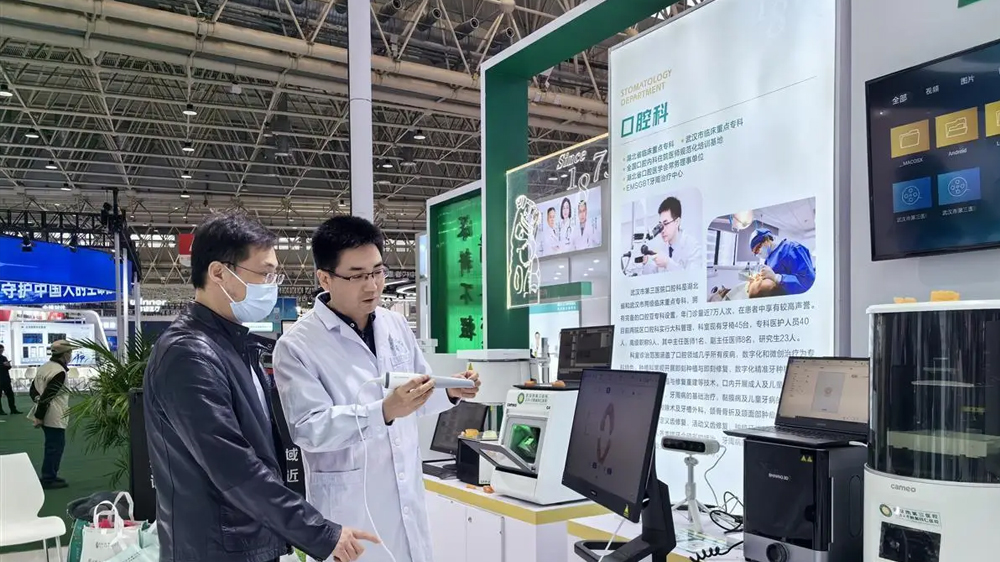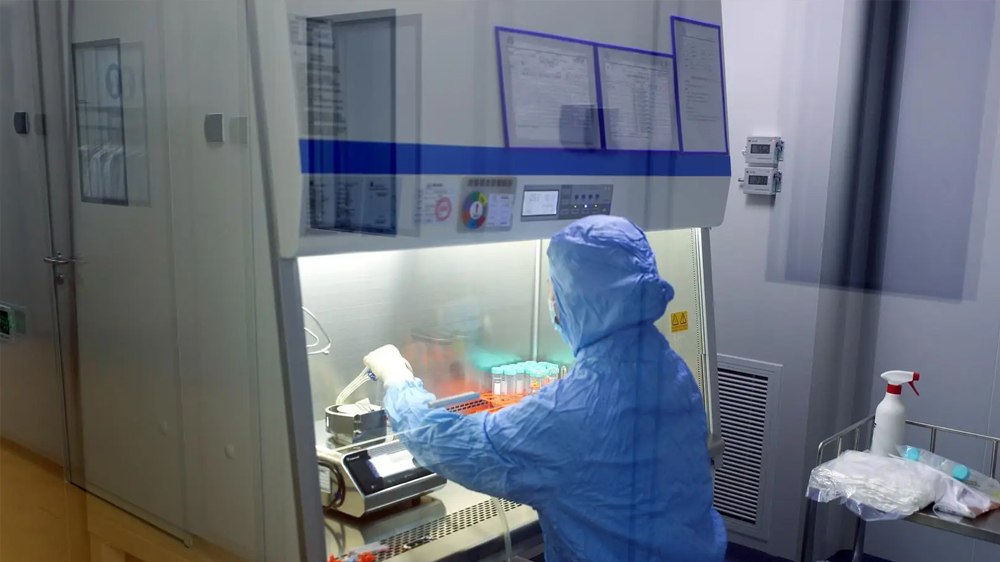жҸҸж‘№зҲ¶дәІ
жқҺзәўйңһ
еҝҪең°еҸ‘и§үе·Іи®ёд№…жңӘи§ҒеҲ°зҲ¶дәІдәҶгҖӮи„‘жө·дёӯеҰӮжҠ•еҪұиҲ¬й—ӘеӣһзқҖзҲ¶дәІзҡ„еҪўиұЎпјҢз«ҹ然еҫҲжҳҜжЁЎзіҠпјҢдјјд№ҺиҮӘе·ұд»ҺжңӘеҲ»ж„Ҹз«ҜиҜҰиҝҮд»–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еңЁйҒҘиҝңзҡ„ејӮд№ЎпјҢеҮӯзқҖи®°еҝҶе’ҢжғіиұЎпјҢејҖе§Ӣз”Ёж–Үеӯ—дёәжҲ‘еҒҮжғізҡ„жЁЎзү№вҖ”вҖ”зҲ¶дәІпјҢжһ„еӣҫпјҢжҸҸж‘№гҖӮ
еҸӨиҖҒиҖҢз®Җжңҙзҡ„йҷўиҗҪйҮҢпјҢдҪҺзҹ®з ҙж—§зҡ„еңҹеқҜжҲҝдҪңиғҢжҷҜпјҢзҒ«зәўзҡ„жңҲеӯЈиҠұгҖҒз№ҒеҜҶзҡ„и‘Ўиҗ„жһ¶дҪңйҷӘиЎ¬пјҢдёҖеҸӘи¶ҙеңЁеўҷи„ҡеҒҮеҜҗзҡ„е°ҸзӢ—дҪңзӮ№зјҖгҖӮзҲ¶дәІе®ҡж јеңЁз”»йқўдёӯеӨ®пјҡз«ҜеқҗеҮіеӯҗдёҠпјҢжӢүиө·дәҢиғЎпјҢи°ғеүӮзқҖеҶңеҝҷзҡ„з©әй—ІгҖӮз”»йқўжё©йҰЁиҖҢдәІеҲҮпјҢд»Өдәәж„ҹж…ЁиҖҢдјӨжҖҖгҖӮ
еҫ®йЈҺеҗ№иө·дәҶзҲ¶дәІзҡ„еӨҙеҸ‘пјҢиҠұзҷҪзЁҖз–ҸпјҢйЈҺдёӯжү“еҚ·пјҢйҡҗйҡҗйңІеҮәеӨҙзҡ®пјҢеҰӮиў«з”ҹжҙ»зҡ„еӨ§жүӢж— жғ…жҺ иҝҮдёҖиҲ¬пјҢжҲ‘еҝғз–јеҸҲж— еҘҲгҖӮеҸ‘й»„зҡ„иҖҒз…§зүҮдёӯпјҢзҲ¶дәІзҡ„еӨҙеҸ‘жІ№й»‘иҖҢжө“еҜҶпјҢжўізқҖж ҮеҮҶзҡ„дёӯеҲҶпјҢдҝЁз„¶з»ҸиҝҮзІҫеҝғзҡ„жү“зҗҶпјҢеё…ж°”иӢұдҝҠгҖӮи®°еҫ—жҲ‘们兄еҰ№жӣҫеңЁзҲ¶дәІйјҫеЈ°еҰӮйӣ·зҡ„зҶҹзқЎдёӯпјҢи°ғзҡ®ең°жҸӘиө·зҲ¶дәІзҡ„еӨҙеҸ‘пјҢеҜҶеҜҶйә»йә»ең°жүҺдәҶд»–ж»ЎеӨҙе°Ҹиҫ«пјҢжӢӣеҫ—зҲ¶дәІдёҖйҖҡе№ёзҰҸзҡ„е—”жҖӘгҖӮзңҹжғіеҶҚж¬ЎжӢҝиө·жңЁжўідёәзҲ¶дәІж•ҙзҗҶеӨҙеҸ‘пјҢеҸҜеҸҲжҖҺеҝҚеҝғзңӢеҲ°д»–еҚҺеҸ‘жҺүиҗҪгҖӮ
зҡұзә№зҲ¬дёҠд»–йўқеӨҙпјҢеҚ°еңЁзңји§’пјҢйҷ·е…Ҙи„ёйўҠпјҢе ҶеңЁи„–йўҲпјҢеІҒжңҲзҡ„еҲ»еҲҖпјҢжҜ«ж— жҖңжғңпјҢзҲ¶дәІеҸӘиғҪй»ҳй»ҳеҝҚеҸ—пјҢд»»е…¶еңЁиә«дёҠж…ўж…ўеҲ»иҡҖгҖӮеңЁзҡұзә№йҮҢпјҢжҲ‘иҜ»еҲ°дәҶиү°иҫӣпјҡзҲ¶дәІе№је№ҙдё§жҜҚпјҢ继иҖҢдё§зҲ¶пјҢж— е…„ејҹе§җеҰ№гҖӮиҝҷж ·зҒ°иүІзҡ„з”ҹжҙ»и®©зҲ¶дәІжҖ§жғ…еқҡеҝҚпјҢеҚҙеҸҲжҡ—йҡҗи„ҶејұгҖӮеңЁзҡұзә№йҮҢпјҢжҲ‘зңӢеҲ°дәҶз”ңиңңпјҡзҲ¶дәІиҲҮжҜҚдәІе’Ңе’ҢзқҰзқҰпјҢжӢүжүҜжҲ‘们兄еҰ№дёүдәәжҲҗ家з«ӢдёҡпјҢзңӢеҲ°еӯҷиҫҲз»•иҶқпјҢ笑дёҚжӢўеҳҙгҖӮзҡұзә№пјҢеҰӮйҒ“йҒ“зЈҒжқЎпјҢеҲ»еҪ•зқҖзҲ¶дәІзҡ„еІҒжңҲз•ҷеҪұгҖӮ
жӣҫз»Ҹиә«еҪұжҢәжӢ”зҡ„зҲ¶дәІпјҢеҰӮд»Ҡ已然еҫ®й©јгҖӮжҸЎиө·дәҢиғЎпјҢе·Іж— еҪ“е№ҙи·ҹзқҖжҲҸзҸӯеҘ”иө°д№ЎйҮҢгҖҒйҷ¶йҶүж“Қзҗҙзҡ„зІҫж°”зҘһе„ҝгҖӮеҗ¬жҜҚдәІиҜҙпјҢеҸ°дёҠзҡ„зҲ¶дәІжӯЈиҘҹеҚұеқҗпјҢдёҠиә«жҢәзӣҙпјҢж‘ҮеӨҙжҷғи„‘пјҢйўҮжҳҫж°”жҙҫгҖӮеҸҜжҲ‘жҳҺзҷҪпјҢдёәдәҶе…»иӮІжҲ‘们пјҢзҲ¶дәІжӣҫдёӢиҝҮз…ӨзӘ‘пјҢеңЁйҳҙжҡ—зӢӯзӘ„зҡ„е··йҒ“йҮҢиң—иЎҢпјӣе№ІиҝҮе·Ҙең°жҙ»пјҢжүӣиө·жІүйҮҚзҡ„й’ўзӯӢж°ҙжіҘжҢӘиЎҢпјӣеёёе№ҙжү“жҹҙпјҢиғҢзқҖеҰӮеұұзҡ„жңЁжҹҙеңЁж·ұеұұйҮҢз©ҝиЎҢгҖӮз”ҹжҙ»зҡ„йҮҚеҺӢпјҢи®©жң¬е°ұеҚ•и–„зҡ„зҲ¶дәІпјҢжёҗжёҗејҜдёӢдәҶи…°пјҢжҲҗдәҶдёҖеј еј“пјӣдҪҶд№ҹж’‘иө·дәҶ家пјҢжүҳиө·дёҖзүҮеӨ©гҖӮ
йӮЈеҸҢж“ҚзқҖзҗҙжқҶгҖҒжҢүзқҖзҗҙејҰзҡ„жүӢпјҢжһҜзҳҰж— еҠӣгҖҒйқ’зӯӢжҡҙзӘҒпјҢжңүж·Ўж·Ўзҡ„иҖҒе№ҙж–‘пјҢзңӢдёҖзңјдҫҝи®©жҲ‘зңјзӘқж№ҝзғӯгҖӮиҝҷиҝҳжҳҜйӮЈеҸҢжӣҫеңЁжҲ‘жҲҗз»©дёӢйҷҚгҖҒи°ғзҡ®зҠҜй”ҷж—¶пјҢй«ҳй«ҳжү¬иө·гҖҒйҮҚйҮҚиҗҪдёӢгҖҒж•Іжү“жҲ‘жҲҗй•ҝзҡ„еҺҡйҮҚжңүеҠӣзҡ„еӨ§жүӢеҗ—пјҹиҝҷиҝҳжҳҜйӮЈеҸҢжӣҫеҒҡиҝҮжңЁе·ҘзҺ©е…·гҖҒжү“иҝҮеәҠй“әж©ұжҹңгҖҒжҢҘиө·й”„еӨҙдҫҝдёӢең°гҖҒжӢҝиө·й“ІеӯҗдҫҝдёӢеҺЁзҡ„зҒөжҙ»иғҪе№Ізҡ„е·§жүӢеҗ—пјҹйӮЈж¬Ўжү¶зҲ¶дәІиҝҮ马и·ҜпјҢд»–з”ЁзҳҰзҳҰзҡ„жүӢжҢҮзҙ§зҙ§жүЈзқҖжҲ‘зҡ„жүӢпјҢж— еҠӣдё”ж— еҠ©пјҢдјјиҰҒе°Ҷд»–дәӨз»ҷжҲ‘гҖӮйӮЈеҸҢжүӢпјҢжҸЎиҝҮдәҶеІҒжңҲпјҢз»ҸеҺҶдәҶжөҒе№ҙпјҢз•ҷз»ҷжҲ‘们зҡ„жҳҜдёҖ笔иҙўеҜҢгҖӮ
иҝҳжҳҜйӮЈд»¶и—Ҹи“қиүІдёҠиЎЈгҖҒзҒ°й»‘иүІиЈӨеӯҗгҖҒж·Ўй»„иүІиғ¶йһӢпјҢиҝҷдҝЁз„¶жҲҗдәҶзҲ¶дәІзҡ„ж ҮеҮҶиЈ…жү®пјҢеӨҡе№ҙжңӘеҸҳгҖӮ
еҸӘдёҚиҝҮиЎЈжңҚе·ІеҸ‘зҷҪиө·иӨ¶пјҢйһӢдёҠжІҫдәҶжіҘгҖӮжӣҫз»ҷзҲ¶дәІж·»иҝҮиЎЈжңҚпјҢеҸҜд»–дёҖзӣҙд»ҘеӢӨдҝӯжҢҒ家гҖҒдёҚи®Із©ҝжҲҙзҡ„и®ӯиҜқеӣһжҲ‘пјҢз©ҝзқҖеҮ 件旧衣пјҢз”ҡиҮіжҳҜжҲ‘们еү©дёӢзҡ„ж ЎжңҚеәҰж—ҘгҖӮи§ҒиҝҮзҲ¶дәІеңЁзҒҜдёӢжӢҝиө·й’ҲзәҝиЎҘиўңеӯҗпјҢи§ҒиҝҮзҲ¶дәІжҷҫжҷ’зҡ„з§ӢиЎЈеёғж»ЎжҙһпјҢи§ҒиҝҮз»ҷзҲ¶дәІд№°зҡ„иЎЈжңҚж•ҙйҪҗеҸ ж”ҫеңЁжҹңйҮҢгҖӮжғіз»ҷзҲ¶дәІд№°иә«иЎЈжңҚпјҢдёҖж—¶з«ҹеҝҳдәҶе°әеҜёпјҢдёҚзҰҒеҝғж„ҹдёҚеӯқе’ҢиҮӘиҙЈгҖӮ
е№ІиЈӮзҡ„еҳҙе”ҮпјҢжІЎдәҶеҪ“е№ҙзҡ„зәўж¶Ұпјӣжө‘жөҠзҡ„еҸҢзңјпјҢжІЎдәҶеҪ“е№ҙзҡ„иӢұж°”пјӣзҫёејұзҡ„иә«жқҝпјҢжІЎдәҶеҪ“е№ҙзҡ„еҒҘзЎ•гҖӮзӮ№зӮ№еӣһеҝҶпјҢеҝҶдёҚе°ҪзҲ¶дәІдёғеҚҒеӨҡдёӘжҳҘз§Ӣзҡ„иӢҰиҫЈй…ёз”ңпјӣз»Ҷз»ҶжҸҸж‘№пјҢжҸҸдёҚеҮәзҲ¶дәІи—ҸдәҺеҶ…еҝғзҡ„ж„Ғз—ӣе–ңд№җгҖӮжҸҸж‘№зҲ¶дәІпјҢзҲ¶дәІзҡ„еҪўиұЎйҖҗжёҗжё…жҷ°пјҢеҚҙж„ҹи§үдёҖеҰӮеӨ©дёӢжүҖжңүзҡ„зҲ¶дәІгҖӮжғіжқҘпјҢзңҹиҜҘеӣһ家зңӢзҲ¶дәІдәҶпјҒ
пјҲйғқе·§еҮӨж‘ҳиҮӘгҖҠдёӯеӣҪзәӘжЈҖзӣ‘еҜҹжҠҘгҖӢ2017е№ҙ4жңҲ28ж—Ҙ/еӣҫ й”Ұи·ғпјүendprint